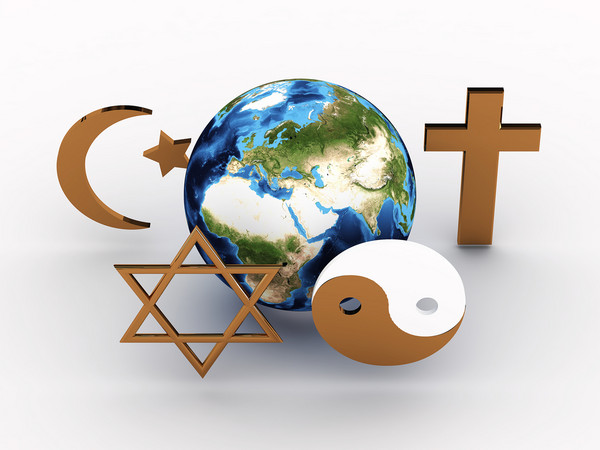
1966年,也就50多年前,一位杰出的加拿大裔人类学家安东尼·华莱士(Anthony Wallace)自信地预言随着科学的发展宗教会全面消亡:对于超自然力量的信仰是不会长久的,这是世界范围内的科学知识的增长和传播的必然结果。华莱士的观点并非少数。另一方面,成型于19世纪欧洲的现代社会科学将其之前的历史经验作为普遍模型。其中核心的有一条——说是假定也好,预言也罢——所有的文化最终都会大致趋向于世俗、西化、自由民主。然而,现实却好像有些背道而驰了。
且不说世俗主义停下了在全球行进的步伐,像是伊朗、印度、以色列、阿尔及利亚和土耳其等国家要么世俗政府被宗教系统取代,要么宗教民族主义者的影响迅速崛起。社会科学预言的世俗化好像已经失败了。
说是失败好像也不太对。宗教信仰和活动的衰落确实在许多国家发生着。澳大利亚最近的人口调查显示“无宗教”人口占30%且比例仍在增加。国际性的调查也印证了,西欧和大洋洲的宗教承认度是较低的。即使是美国这样宗教性很强国家,无信仰者也有了抬头的趋势。无神论者的比例达到了历史最高(如果“高”用在这里合适的话)——3%左右。然而,以全球来说,认为自己拥有宗教信仰的人数仍然是很多的,并且根据现在的人口趋势,短期内宗教人口是增加的。这还不是世俗化理论唯一失败的地方。
科学家,知识分子和社会学家期待现代科学的传播会推动世俗化,即科学成为世俗化的动力。但显然并非如此。如果我们观察那些宗教势力活跃的社会,他们的共同点和科学没什么太大关系,而是对生存安全的需求、对动荡生活的惶恐和前途未卜的畏惧。构建一个社会安全系统可能和科学进步有关,但这种关联是松散的,此处美国又是一个例子。美国可以说是现在世界上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地区了,但同时也是西方社会中最为宗教化的国家。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大卫·马丁(David Martin)在《基督教的未来》(The Future of Christianity 2011)总结道:科学进步的程度与宗教影响、宗教活动的减少没有确定的联系。
让我们再来看看那些世俗化进程中遭遇巨大阻碍的社会,科学和世俗化之间的关系就更加难以琢磨了。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积极倡导世俗化和科学理念,在现代化进程中大力支持科学教育。尼赫鲁自信地认为无论是印度教中对吠陀历史的憧憬还是□□梦想的神权政治都将屈服在势不可挡的世俗化浪潮之下。“时间总是向前进的单行线”他宣称到。然而紧接而来的是印度教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尼赫鲁是大错特错了。科学对世俗化的作用在这儿引火上身,反而成了抵抗世俗化的炮灰。
土耳其是个更明白的案例。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者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像很多先驱者一样是坚定的世俗主义者。他坚信科学注定是要代替宗教的。为了确保土耳其走上正确的历史道路,他将科学,尤其是生物进化论,置于这个新生政权国民教育的核心地位。于是,进化论体现在阿塔土克的整个政治方案(包括世俗化)之中。国内的伊斯兰政党试图对抗这位国家创始人的世俗化理想,同时也抨击其进化论的教育。对他们来说,进化论是和世俗唯物主义相关的东西。这种国内氛围最终导致了六月(2017)土耳其政府把进化论内容从中学课本删除的决定。再一次的,科学成为牺牲品。
美国代表另一种不同的文化语境。表面上问题的关键是创世说和进化论的争论。可实际上,神创论者关注的更多的是价值观。在美国也一样,反进化论者的部分动机是认为进化论是一个幌子,背后是世俗唯物主义及其相伴的整个道德理念。和印度、土耳其的情况一样,世俗主义实际上伤害了科学。
总之,全球世俗化的浪潮并非大势所趋,以及它发生的地方也很难说和科学有关。甚至那些试图利用科学推动世俗化的尝试反而会伤害科学。"科学导致世俗化"的理论没有通过实证,把科学当做世俗化的手段也不见得是个好办法。既然"科学"与"世俗化"摆在一起如此勉强,又怎么会有人相信着这一点呢?

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
历史上,“科学取代宗教”的想法有两个来源。其一,19世纪对于历史的进步主义观点,代表人物是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他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会经历三个阶段——神学(théologique)、形而上学(métaphysique)、实证科学(scientifique)。孔德创造了“社会学”一词,他想减小宗教的社会影响而用一种新的社会科学代替。孔德的影响延伸到“青年土耳其党人”(young Turks)以及阿塔土克。
19世纪还建立了科学与宗教的“冲突模型”。它将历史视为人类思想演化中两股潮流的冲突——神学和科学。这一描述来自安德鲁·□□森·怀特(Andrew Dickson White)颇具影响力的著作《科学与基督教神学的战争史》(A History of the Warfare of Science with Theology in Christendom 1896),标题就概述了作者的主要理论。怀特的作品以及更早些的约翰·威廉·德雷柏(John William Draper)的《宗教与科学冲突史》(History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Religion and Science 1874)牢靠地建立了思考科学与宗教历史关系的一般模式——冲突论。两本著作都被翻译成诸多语言。德雷柏的书仅在美国就被印刷超过50次,被翻译为20种语言,在曾经的奥斯曼帝国晚期成为畅销书籍。在那里,阿塔土克获知了科学代替宗教的观点。
如今,人们不再自信地认为历史是循着一级级阶梯走向唯一的目的地。大多数科学历史学家也不再坚持科学与宗教之间有着持久的冲突——尽管这种观点在大众之中依然流行。那些著名的冲突事件,比如伽利略事件,转而解释为政治与个性之间的冲突,而不仅仅是科学与宗教。达尔文当年有着重要的宗教立场的支持者以及反对他的科学工作者,反之亦然。许多其他的声称的科学-宗教冲突的例子也被发现有捏造的成分。实际上,与斗争相反,实际的历史经验往往体现出科学与宗教的相互支持。在现代科学诞生初期的17世纪,科学依赖于宗教的合法性。而在18、19世纪,宗教对科学的普及也有帮助作用。
科学与宗教的冲突模型对于过去的看法是错误的,当它与世俗化的期待相结合,又对未来给出了错漏的预示。世俗化理论在描述和预测两方面都失败了。那么真正的问题来了:为什么还总能遇到这种冲突论的拥护者呢。其中许多还是著名的科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英国著名演化生物学家,新无神论的四骑士之一)对此问题旳思考就不赘述了,但他绝不是唯一的。史蒂芬·霍金认为“科学终会胜利,因为它是正确的”;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美国著名神经学家、哲学家,新无神论的四骑士之一)宣称“科学一定会摧毁宗教”;斯蒂芬·温伯格(Stephen Weinberg,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觉得科学已然削弱了宗教的宗教确定性;科林·布莱克莫尔(Colin Blakemore,英国神经生物学家)预测科学最终会使得宗教可有可无。然而历史证据显然不支持他们的观点。事实上,这说明他们也被误导了。
那么他们为何坚持此观点呢?答案是政治性的。暂且把对古朴的19世纪的留恋放在一旁,我们要看到人们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惧、对神创论的愤怒、宗教权力与否认气候变化的势力的勾结令人厌恶、科学的权威性渐受侵蚀使人忧心忡忡。我们对这些深切关心,但不可掩饰的事实是:它们的产生是规范承诺(normative commitments)对于讨论的无益的侵扰。这种一厢情愿——希望科学战胜宗教——不能代替对于当前现实的清醒判断。继续这种宣传可能会适得其反。
宗教不会很快消逝,科学也没法打败它。要说科学对宗教有什么作用,科学会逐渐威胁到宗教的权威性和社会合法性。基于此,科学需要尽可能的结交盟友。它的倡导者越多来自宗教的敌人越少,或者说坚持科学和世俗化的联姻仍然是走向一个安全的未来的唯一道路。
本文译自 Why religion is not going away and science will not destroy it | Aeon Ideas,由 dingding 编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