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Nosleep:废墟余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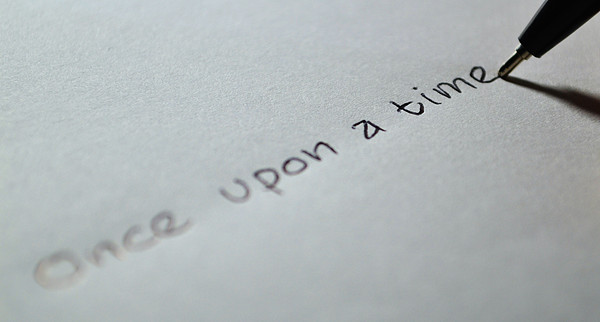
credit:锐景创意
【原标题】我的一位学生上交了一份让人不安的“身边的历史”课后作业
作为一名初中历史老师,每个学年结束后布置给学生的“身边的历史”作业算是我最讨厌的教学任务之一。孩子们会被要求围到他们祖父辈身旁询问他们所能记得年代最久远的一份记忆,并用各种方法记录下来(当然这同时也是个能轻易提高他们GPA的简单途径)。
我做这件事已经有十七年了。所以当今年他们把作业交上来时,我并没有对此报以太大的期望,只求它们不要太过沉闷就好。毕竟这也不是个特别惹人瞩目的班级。
所以我到家,给自己倒上一杯酒,再次准备度过一年一度读着诸如“我在你这个年龄时一共就只有两条裤子”,或是“有次我兄弟因为把棒球打到了隔壁邻居院子里,结果被他用报纸打了一顿”故事的漫长夜晚。当然了,这些故事通常还自带评论。老年人总是不能意识到他们言语当中其实饱含着性别和种族歧视,但我也只能冲其一笑罢了。
我班上有个女生,在这里我准备叫她Olivia。矮矮的,胖胖的,安静的,毫不起眼的Olivia。可能正因为如此,我自以为她的故事也将一如既往地染上她自身的特点,才会对那个晚上我所看到的故事如此恐慌。
Olivia交上的作业是两张光盘,于是我打开了上面贴着“采访”的一张。随着几下屏幕抖动,一个客厅的轮廓渐渐呈现在我面前。简直是个囤积者的天国。Olivia捧着笔记本,蜷缩在扶手椅上,看上去就像只被吓坏的小动物。在她面前坐着的是个一脸严肃的男性,点着烟,眼带期待地看着她。
“可以开始了,”女性的声音从镜头背后传来。Olivia清清喉咙,挂上一副严峻的神情,看了眼镜头,又再次把目光转到那个男人身上。
“坐在这里的是我的叔祖父Stephen,”她的声音几乎细不可闻,“他将会和我们分享他以前从军时的经历。”
Stephen表现出一副情愿回到战壕也不愿待在这的神情,但他坚持了下来。
Olivia开始提问。她毫不让人意外地按着我事先和他们说好的建议问题开始逐字逐句地往下念。老人简短地回答着她的问题。有那么一两次,我能听见她母亲在摄像机背后悄声对Olivia说话,让她大声点。无聊得要死。
可能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会被Olivia的下一个问题挑起了好奇心。她把笔记本放下,直视着Stephen,“你喜欢参军这件事吗?”
这个问题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烟雾朦胧中,伴随着叹气声,Stephen再次喷出一口烟。“一点也不。不过我倒是很高兴能有机会远离自己的家乡。”
“你们去的哪?”
“巴尔干半岛地带。”
“这样啊,”她说。我暗自怀疑Olivia其实对巴尔干半岛的历史一点也不了解,而这种怀疑也在下一句话中得到了证实。
“那是不是和这里完全不一样啊?”
“没错。”
Olivia的妈妈清了清喉咙,我猜她是想暗示Stephen能再多说几句。
但Olivia并没有因此受挫。“叔祖父,”她问道,“你在军队时经历过最惨的一件事是什么啊?”
眼前的这位老人突然缓慢拉直身子,一手把烟蒂狠狠地摁在面前的烟灰缸中。“等我一下,”他嘴里嘟哝着。画面暗了下来。
影像再次浮现,Stephen再次回到镜头前。他面前的咖啡桌上多了几张过塑的信纸,除此以外一切别无变化。从这个角度,我能看到他悄悄握了握拳。
“我参军时还小,”他看着Olivia,“和你哥差不多大。”他说。她点点头。“我从未真正上过前线,上头布置的任务也只是让我们到几个被内战摧毁了的东欧国家去。那里乱得一塌糊涂。我常常觉得我就是个清洁工,操他大-”
“咳咳!”妈妈在镜头背后作出抗议。
老人叹了口气,重新把目光转到眼前的信纸前。“我所在的部队被派遣到一所被严重摧毁的学校。破旧的窗户,毁坏得如同洞穴的房间,诸如此类 - 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最让我受到触动的一点是早在我们到来前,这所学校已经持续这样的状态好几年了。它就那样被搁置着,没有人愿意为它动哪怕一根手指。孩子们对此直视无堵,只会径直朝你走近问你要钱,或是别的什么逼玩-”
镜头径直指向地面,我能听见Olivia的妈妈在严厉地悄声对Stephen训话。声音很小,我没办法仔细听清楚他们的对话,但我大概能猜得出来。
“所以你他妈到底要不要听这个故事了?”我能听见Stephen在咆哮。“我他妈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不关你事。”
“妈,”Olivia□□,“请你别再打扰我们了好吗?”
“这个是要在课堂上放出来的吧?”
“不用,只要交给老师就好了的。”
“再说他总不可能从未听过脏话吧?”Stephen有力地反驳。虽然说我不是“他”,但他说得不无道理。
摄像机重新被摆正,镜头聚焦到熟悉的客厅上。
“算了,无关重要的东西我说得太多了。”Stephen低声抱怨。他拿起手边的其中一张信纸,“在学校的地下室里,我找到了这些信。我不懂它的意思,但我有个哥们给我翻译了下。我会先给你们读一下这个故事,然后再告诉你们我在地下室里看到的情景。”
一阵寒意掠过。镜头聚焦在Stephen和他的信上。曾经坚定而有力将烟头扼杀的手如今忍不住颤抖。这是他的故事。
亲爱的陌生人,
我从未爱过我的祖国。太多的骚乱,太多的战争。太多打着爱国主义大旗却只为了满足个人私心企图分割这个曾经一度伟大的国家的灾祸。我从未在乎过这个国家在地图上所被称呼的名号。我只想尽可能远离这些无意义的争斗。
但不是因应战争而来的袭击与暴乱夺走的我妻子和孩子的性命。是疾病。我的孩子有幸死得很快。但Nadja,她熬了很久。我看着他们发病,我看着他们死去。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一切的发生,我什么都帮不上忙。我想我唯一的安慰也只是他们最后的每时每刻我都有陪在他们的身边。我没有再去工作。也没有人来找过我。我怀疑会不会有人注意到我的消失。学校就在隔壁,透过家里的窗户就能看到,每天过去工作几个小时然后赶紧跑回家照顾他们也不是件难事。但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只不过是个清洁工。对这个世界而言,我和我对自己家庭一样毫无用处。
我带过Nadja去医院,但路程太远太折磨。她在到家的那个晚上就死了。
我的Nadja和孩子死后的那段日子…说实话我已经不大记得了。我躲在自己的房间,不吃不喝不睡,一直在想要不要随他们而去。尽管这个奖赏无比诱人,但我更多也只是放纵在自己的无能为力当中。
唯一还陪着我,唯一还让我能保持理智的只有这部收音机。我一直让它开着。尽管我没有听懂过它传出的讯息 - 我能收到最清楚的频道说的是英语(我猜是),而我不会英语。但那些话语,那些音乐,那些真正的知识,那些在这个罪恶之城以外还有别的世界的真相让我支撑了下来。
我不知道是过了多久我才重新意识到阳光的存在。我饿得发晕,我需要去找点能吃的东西。我的收音机当然得跟在我身边。在我重新振作以后,它一直和我在一起。无论我或眠或醒,它会一直对我说话。我不知道它在说什么,但我知道没有了它我情愿去死。
在我找到水源与食物以后,我突然意识到我生命中唯一余下的意义只剩工作了。于是我回去了,我在隔天再度作为一个清洁工回到了学校。
没有人对此表示意外。学校的职工们都知道Nadja已经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没有人在我人生中最艰难的日子还缠着让我回来心怀感激。教师们没有对我说些什么,但我们会在教学楼相遇,然后互相冲彼此笑笑。也许就是因为能获得这点尊重我才会重新回来工作。
没有我,这个地方乱得一塌糊涂。我从柜子里再次找出清洁工具,开始清理。我知道大家都欢迎我回来。最让我高兴的一点是没有人对我的收音机有过意见。我总是把它带在身边,音量调到最小,好让它不要干扰到学生们学习。没有人抱怨。我猜大家也喜欢它。
教学楼不大,但要做的事可不少。地板老是沾满污迹,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拖地。孩子们就爱捣乱 -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需要我的存在。有的时候我不得不把东西搬开才能把每一寸地板都擦得闪闪发亮,但我为我自己感到自豪。
我还得干修理的工作!这所学校不时会有需要修整的地方,而我很乐意为此帮忙。有几天我在忙着修一套桌椅 - 我在学着哼收音机上的新歌时它就那样在我面前塌掉了。别的日子里我会忙些更严重,更有结构性的修理工作。当我在干这些事时,我真实地感到自己是有用的,是这个大机器里的一颗不可缺少的小螺丝。这个学校怎么能少得了我呢?这花了我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但我终于又再次觉得人生有了意义。
校园的后方有一个储存室,里面装满了腌制食物。我没有工资,但他们告诉我可以随便拿走里面的东西。这很好,反正我要钱也没用。以前我还会把食物带回自己离学校一墙之隔的家,但后来我开始直接睡在学校地下室。没有人留意到我在这里。我守护着这所学校,它是特殊的。
每当我的脑海再度被Nadja和我们的孩子占领,我就把收音机的音量调高将脑海中鲜活的影像洗去。每一次,每一次这都能效奏。
但除了这次。但除了这个早上。
因为今天早上我醒来时听到的只有一片死寂。
我翻来覆去地检查着它。我的收音机。我也实在记不得它陪了我多久。你是终于活到了你寿命的尽头,不得不和我说再见吗?这一整天我都在试着修理它,但其实今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哭。我不能没有它,没有它我就不再是我自己了。
我给了自己一个期限,直到日落。如果日落前我还是无法将它修好,我将会结束我自己的生命。我之所以提笔写下这些,是因为我已经快要看不见光了。我想我知道自己将会面临着怎么样一个命运。
我有想过要最后一次走在我心爱的校园里,和学生们和老师们说声再见。我知道他们会想我的。但我动不了了。收音机死了。我的收音机死了。我哪里都去不了了。
眼睛流不出眼泪了。我没办法呼吸。我把胃里吃的东西都吐出来了。我又开始晕了。就像Nadja死的时候一样。我知道我的时候快到了。
在我结束自己性命之前,我会关上了房间的门,在门把手的位置放张椅子挡住通向里面的路。这是地下室唯一的房间,我真幸运,它还有个小窗户能有光让我看清楚自己将要做的事。如果有好心人想要来找我,也许他们会发现门是锁着的,也许他们会发现门后传来我腐烂时的臭味,然后他们会走开,他们会忘了我这个人的存在。他们不应该看到这样一幕。
但我把这些笔记和我的收音机都留在了门外。好心的陌生人,如果你正在读着我的遗书,我有个最后的卑微的请求:请你修好它吧。救救我的收音机。它不应该就这样死在睡梦中。对不起,我没能把它救活。
我准备好要到天堂和Nadja和小Ludmilla重聚了。希望学校能找到另外一个像我一样爱它护它的清洁工。
时候到了。别忘了我的收音机。
Stanislav
镜头拉远,眼中有泪的Olivia再次出现在屏幕上。“谢谢你,叔父,”Olivia的妈妈哽咽着,“我想这就够了。”
“等一下!”Olivia打岔,“还没完呢。叔祖父你在地下室找到什么了?”
没等老人开口,画面就忽然变暗,影像消失了。我满心迷惑。怎么了?他到底看到什么了?
我立即想起Olivia交上的不止一张碟。还有一张,还有一张没有标签的,希望我的问题能在那找到解答。
第二张碟中没有影像,只有音效。我首先听到的是Olivia的声音。
“Gerrity老师,你好。我想先为我妈妈的行为道歉,她拒绝为余下的部分继续录像。但我悄悄用自己的手机录下了叔祖父所说的话。我还记得今年年初时你曾经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写就的。”她的呜咽声隔空传来。“但历史不应该只有胜利者,失败者也同样有被记录的权利。尽管他们可能不如人妙,尽管他们可能一无是处,尽管他们可能没有赢过哪怕一场人生的战役。这几晚我都没能睡着,我一直在想Stanislav和他的收音机。我想你应该听听叔祖父余下的话。”
眼泪也同样涌上了我的眼睛。她的话语当中带着一种虔诚而直接的美感。我同时也感到受宠若惊,她居然会记着我说过的一些老生常谈,而那仅仅是因为我的历史老师也是这么和我说的。
在我变得过于自傲前,音频继续,故事再度开始了。
“行,”恼怒的声音从中传来,“你要想听完整个故事,可以,但这已经超出学校要求的范围了。”
“让我说完吧,”老人加入对话,“如果这个故事对你来说太过沉重,那你到厨房去好了,让Olivia听完她想听的就是了。”
我能听见Olivia的妈妈嘟囔着走开的声音。现在房间里只有Olivia和她的叔祖父。我想她一定很兴奋吧。
“所以你找到那个收音机了吗?或是说它已经被毁在了战火中?”
齿轮滑过火石,老人再度点燃了一根烟。“那封信,”他慢慢说道,“是署有日期的。”
“什么时候?”她追问道。
“在我们到来前的两个星期。”
“但你不是说那所学校两年前就已经被摧毁了吗?”
“对,”老人回答。“你说的没错。”
一片死寂。我能感到鸡皮疙瘩开始在我手上成形。过量的信息影像在我脑海中堆积如山,我无法把它们拼凑成哪怕一个单字。但老人毫不费力地说出来了。我想他这一辈子都在想同一个问题。
“这个男人,这个Stanislav。他在一个废墟,一个被遗弃了的校园里搬着碎石、擦着血污,但却深信他在做的只不过是扫开堆积的灰尘、擦掉弄洒的饮料。他会对走廊里遇到的死人微笑,并且相信着他们也在对他做着同样的回应,相信他们喜欢他的收音机。他会把尸体搬开,仅仅是为了能擦干净尸体底下的地板。屋顶塌了一半,他在下雨时肯定会淋得浑身湿透,但他像是没有感觉一样,一句话也没提过。”Olivia的哭声隔着音频传来,“我找到了他所说的那个储存室。里面都是盐腌的食物,全发霉了,吃起来估计连猪食也不如。”
“你-你有看到他的尸体吗?”
“嗯,就挂在天花板上。但看上去仍然像是还活着一样。他还没腐烂,毕竟才死了几周。”
“他看上去走得安详吗?”她的声音中充斥着绝望。
“我不知道。他浑身散发着恶臭,脸是蓝色的,眼球暴凸,像这样。”
“那他的收音机呢?”
“它在那。”
老人深吸一口烟,
“它还在那,是开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