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
基因驱动——让蚊子自我灭绝(二)
注意你的梦想
帝国大学团队预想在三年内研制出可用的基因驱动,但盖茨基金会把试验时间定在了2026年。德国联邦自然保护局的生物安全专家,Margret Engelhard指出,这次试验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些挑战,比如在释放转基因蚊子之前需要进行科学评估,预测这些蚊子在野外会如何活动,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物种等等。帝国大学环境政策中心的Tilly Collins已经在研究中证明,没有任何物种只吃冈比亚按蚊(冈比亚按蚊是三种能传播疟疾的蚊子之一,也是非洲蚊媒病最大的元凶),也就是说,如果消灭了冈比亚按蚊,不会有其他物种因此饿死。维多利亚湖湖边的一种吸血蝙蝠特别喜欢吃吸满血的雌性冈比亚按蚊,但假如没有,也能吃其他蚊子。
学界还在验证这一发现,同时也在探究是否有物种仅依靠吃冈比亚按蚊的孑孓为生。至今还没有任何证据说明灭除三千种蚊子中的一两种会对生态有什么显著的影响——唯一的附带受害者可能是疟原虫。
那么如果基因驱动跑到了其他物种身上呢?理论上基因传播需要进行交配,产生后代才能传播,基因驱动会留在同一个物种内,因为不同的物种是不能产生后代的。(只要你不是大豆和人类交配的产物,转基因大豆的基因就不会跑到你身上。)但是doublesex基因存在于按蚊属的所有16个种中——之前说了,这个基因很古老,没怎么发生过突变。因此的确有那么一点点可预测的可能,这些蚊子会杂交,把基因驱动传播到其他物种中。这个几率很小,但值得注意。(译者注:其他物种没有doublesex,因此最坏情况是我们一不小心弄死了所有按蚊,并不会变成末世电影的情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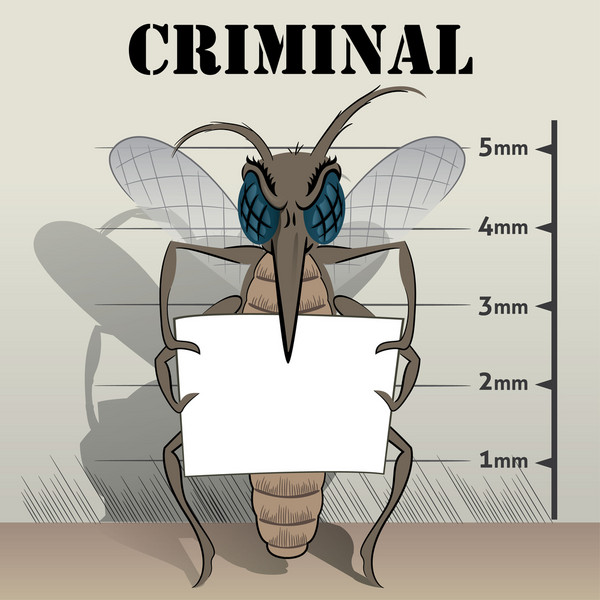
非洲联盟下属机构“非洲发展新合作”建议非盟成员国支持这项研究,以验证这项技术在非洲的可行性——包括对风险的全面评估,并寻找降低负面影响的方法。“目标:疟疾“想让当地人理解为什么他们要研究并释放转基因蚊子,在此之后,他们会在布基纳法索放生一批不育雄蚊。这次试验是为了让科学家理解蚊子的移动(迁移)方式,但由于没有插入基因驱动,这次实验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
“目标:疟疾”的基因驱动计划会使人道主义行动前进一大步。这个计划经过了精心设计,慈善家们也慷慨解囊,国际社会也对计划进行了细致的审查。这个计划受到了政府支持,也激励了新一代科学家。没有大规模反对、没有明显的替代方案、没有严重的技术缺陷,这个计划不会停止。即使是反对基因驱动的ETC Group的发言人Jim Thomas也承认,根除疟疾是基因驱动技术的“最佳应用目标”,的确是一件好事。
但ETC Group等组织担心的是,用基因驱动治理疟疾会给未来不那么严谨的、会出现问题的、甚至恶意的用途大开方便之门。例如孟买的Tata慈善信托给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捐助了7000万美元,用以研究如何通过基因驱动技术使农作物更抗旱。如果这项技术和“目标:疟疾”一样可预测、可控、管理良好,当然可以使农作物熬过气候变化,甚至还能减少杀虫剂和除草剂的使用。但现实证明,没有什么技术能做到“可预测、可控、管理良好”。Jim Thomas担心人们不小心把野生的植株也一起转化了。“这个开关一旦打开就关不上了。”
在一篇2016年的报告中,美国国家科学院指出,为了农业生产使用基因驱动会对其他人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例如长芒苋这种杂草在美国已经成了农民的心头大患,因为它已经产生了对草甘膦(常用除草剂)的抗性,但同为苋属的植物在墨西哥、南美、印度和中国都是能吃的蔬菜。(译者注:长芒苋在中国也是入侵物种,但只在北京的几处发现。米苋可好吃了)美国农民可不敢承担灭绝其他国家经济作物的责任。
还有人担心基因驱动技术会被武器化。当然,这个技术不可能直接用在人身上,因为人繁育后代周期太长,一次也生不了几个,几代后才奏效的“武器”根本起不到威胁作用。但基因驱动技术可以用在啮齿类动物或者昆虫身上,使它们更暴躁或者更容易携带传染病。五角大楼国防高级研究计划机构(DARPA)正是为了防止这种攻击,自己开展了对基因驱动的研究。DARPA“安全基因”计划的项目经理Renee Wegrzyn称,他们的工作是为了防止出现“技术上的变故”,无论有意无意。这个项目资助的某个研究团队正在研制CRISPR酶,希望借此抑制基因驱动的正常工作。
许多组织都在尽力使基因驱动更可用、更安全。一个选项是开发“免疫驱动”,一旦原有的基因驱动出现异变,可以用免疫驱动祛除。还有一个选项是降低基因驱动传播的能力。现在的基因驱动是“自驱动的”,即切割染色体的和被粘贴在切口上的是同一个基因驱动,但我们没有必要这么做。MIT的Kevin Esvelt设计了“链式”基因驱动机制——把一组基因驱动连接起来,第一个基因驱动切割的切口会被第二个基因驱动占据,第二个基因驱动的切口被第三个占据,以此类推,直到最后一个基因驱动插入染色体,而这个基因驱动就是真正起作用的基因驱动。由于“上游”基因驱动没有被植入染色体,就会在一代代繁衍过程中消散,直到留下了最后的“目标”基因驱动。
(译者注:举个例子,如果把科学家直接修改的那一代成为“第0代”,那么在第1代,第一个基因驱动因为没有被植入染色体,则第1代都不会携带第一个基因驱动;第1代繁衍第2代时,由于第一个基因驱动已经没有了,第二个基因驱动就不会被植入,则第2代不会携带第二个基因驱动;以此类推,在第n代,前n个基因驱动都会消失。)
我们可以把链式基因驱动想象成一个扛着卫星或弹头的分级火箭,每一级都会把卫星/弹头推得更高,而每一个基因驱动都会把“目标基因驱动”在种群中扩散得更远。而一旦所有的助推火箭全部脱离,卫星/弹头就会完全受引力控制,无法再上升。因此基因驱动不会无限传播下去,仅仅在短期内起效,几代之后就会完全消失。我们可以把链式基因驱动看作安全版的基因驱动。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不能排除在安全措施起效前,基因驱动会对生态造成不可逆损害的可能。学界对入侵物种已经研究了数十年,用相同的模式考虑基因驱动,这种可能是完全存在的。由于每个基因驱动都是独一无二的,作用染色体不同,目标物种不同,影响的种群不同,影响的生态体系不同,因此我们需要一套规范来管理每一种基因驱动,可惜这套规范尚不完善。2014年MIT的Kenneth Oye和他的同事在Science中发表了文章,指出了美国相关规范众多的漏洞。
这套规范不仅需要政府部门间合作,还需要政府间合作。2003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会议(CBD)通过了Cartagena生物安全协议,规定了转基因生物的传播规范,但规范中没有明确基因驱动应该如何进行规范——而且美国根本没有通过这份协议。ETC Group和其他组织曾经尝试通过CBD禁止研究基因驱动,但是这份提案在2016年坎昆会议中被否决了。
本月末,埃及将会进行基因驱动的实地试验,也有一些组织尝试阻止这次试验,但八成也会被否决。至今人类还没有达成共识,我们究竟愿意承担多少风险,我们究竟应该影响自然到什么程度。一些组织希望重新引入在某些地区灭绝的生物,引发了大量争议,而基因驱动同样会引起“守护自然”派与“驯化自然”派的争吵。
当然,反对派还有时间,盖茨基金会要过八年才会进行实地试验,或许可以用八年时间找到更好的替代方案。不过假如两年前基因驱动技术被直接禁止,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有意思的替代方案了。
至少对于疟疾而言,人们对于采用基因驱动技术的态度还是积极的。这并不意味着未来不会有其他变故,也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提起警惕。采取基因驱动技术比挥一下电蚊拍要复杂得多,但对数百万受疟疾威胁的非洲人民而言,如果他们无需再担心蚊虫叮咬,这会改变他们的一生,也会改变世界。
本文译自 the Economist,由 花生 编辑发布。

